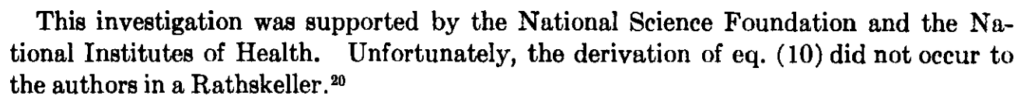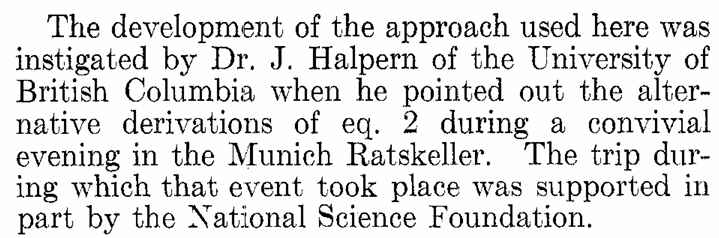日本的现代物理化学
水岛三一郎(Mizushima Sanichiro)在Annu. Rev. Phys. Chem.上介绍日本物理化学的历史,努力从日本文化解释,为什么日本研究的课题和对象跟西方不一样。他也提到了中国思想家怎么反思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他引用了任鸿隽的文章,但有趣的是他好像误会了任是一位女士。我手头上有任鸿隽的文集,但是找不到单独的一篇文章表述了水岛三一朗引述的所有内容。大致上,按照水岛三一郎的引述,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的中世纪文化过于强调”what to do over what to know“。我觉得这个描述十分精确而且悲剧性地统治至今。任鸿隽确实在《建立学界论》中说:
国人向学之诚。自近世科学之术。愈益发达。凡人群所待以为用之智识。有条理伦脊可抽绎者。莫不列为专科。从事研究。明而政治经济。玄而哲理数术。大而建船筑路。细而日用服食。皆得于学校教育占一席焉。其教育之旨。多在致用。致用之极。于是有浅尝肤受。得一能自给。充然自以为足。而无复深造之想者。夫今之科学。其本能在求真。其旁能在致用。上治之国。其制度厘然。物质灿烂者。无非食科学之赐。致用之无害于科学。又何待言。顾无委心专志。发愤忘食之科学家。积其观察之勤。试验之劳。思辨之能。为之设立公例。启示大凡。令后人得循序渐刊以抵高明之域。则近世欧洲学界。仍如中世之黑暗可也。是故建立学界之元素。在少数为学而学。乐以终身之哲人。而不在多数为利而学。以学为市之华士。彼身事问学。心萦好爵。以学术为梯荣至显之具。得之则弃若敝屣。绝然不复反顾者。其不足与学问之事明矣。
水岛说,日本引入西方新思想的时候没有完全替换老思想。在明治维新的时候,知识分子圈就常说要“ Japanese spirit and Western technology”,颇似我国清末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跟我们的历史对明治维新“全盘西化”、推行“欧化主义”、“脱亚入欧”的评判相左。有说,《脱亚论》一文虽发表于明治十八年(1885),但此文自昭和26年(1951年)以后才在日本民间广泛流传,在此之前似乎并未对日本文化及明治维新的现代化带来巨大影响。但上述说法并非完全正确,《朝野新闻》在脱亚论一文发表后,针锋相对地发表了社论,希望中日两国能平等合作,批评了当时《时事新报》为代表的对清开战论。只是《朝野新闻》对“脱亚论”的反驳在当时很快便湮没在了蔑视中国、主张开战的强硬舆论声音之中。
日本高分子科学之父与维尼纶
桜田一郎被认为是日本高分子科学之父。1928年留学德国,先师从W. Ostwald,后来跟K. Hess。在这个年份正是Staudinger的大分子概念在争议中逐渐接受的节骨眼。Hess是低分子观点的坚持者。但桜田回国后却成了高分子科学的建设者。另一个日本高分子产业的先驱——倉敷絹織(现可乐丽)的友成九十九,也是Hess的学生。在低分子学说者那里学习,回来都成了高分子人。
日本的化纤工业很强大,很大程度是桜田一郎本人的研究积累和二十世纪历史的影响。1938年(昭和13年)10月27日,杜邦宣布“人造丝”(尼龙)产品。当时日本蚕丝对美出口量很大,是日本外汇主要来源。在军国主义“富国强兵”政策下,日本正急着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要靠蚕丝出口挣的外汇来买先进的机器、仪器乃至武器。因此尼龙的问世对日本的军事扩张冲击很大。
尼龙问世后,桜田虽马上做了一些尼龙X射线衍射分析其晶体结构的研究,但很快就转而研究聚乙烯醇为原料的纤维。这是因为这种高分子在日本已经有一定的研究积累。朝鲜的李升基当时在日本就研究过聚乙烯醇的皂化反应,当时原料聚乙烯醇在日本已实现试生产,且日本已掌握先进的湿法纺丝技术,因此聚乙烯醇潜在的水溶性使得它更适合当时的纤维产业现状。桜田与本升基还有川上博等人通过改良醛处理工艺,又改善了纺后的耐水性(所以其实是聚乙二醇缩醛)就在尼龙问世的一年后,聚乙烯醇纤维工艺由李升基在日本化学纤维研究所的研讨会上发表。当记者闻讯询问新纤维名称时,桜田当场命名为“合成一号”。而“维尼纶”其实是来自李升基回国后起的“维纳纶”名称。
1945年日本战败后,韩国知识分子陆续返国,李升基在战后担任首尔大学教授。由于韩国当时并不重视这种人工纤维的量产,加上李升基对美军军管首尔大学的做法十分反感,他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于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时接受了朝鲜的延揽,北上平壤。
朝鲜战争停火后,朝鲜开始进入重建阶段,李升基开始在朝鲜制造维尼纶。由于朝鲜的气候和土地面积不适合种植棉花和提供大量羊毛,加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法提供足够的棉花和羊毛,朝鲜政府对人造纤维的作用非常重视。1961年5月6日,2.8维尼纶联合企业所在咸兴市开工投产,这一成就被作为主体思想领导的典范而被广泛宣传,维尼纶由此被朝鲜称为“主体纤维”,除去用于生产衣物外,还用于生产鞋、绳索和被褥,在朝鲜获得了广泛应用。1983年,朝鲜又在顺川市建设了第二家大型维尼纶工厂。
其他国家的情况
美国大陆的高分子科学似乎以1951年Flory的经典教材的出版形成了一道“近代”与“现代”的分水岭。大约在1951年后,连续介质力学的理性化开始了。虽然Mooney在四十年代就给出了它的橡胶弹性公式,但是Rivlin在50年代作了数学形式的严格化。这种严格讨论的其中一个具象化结论就是:不可压缩材料只允许个别模式的形变。但是直到Ogden在70年代再次考虑这个问题之前,以Flory为主导的高分子化学界貌似一直没有重视这个层面,而仍然视Mooney–Rivlin模型为“现象学模型”、“缺乏明确的分子基础”。很遗憾,这种叫法,仍保留在我国当前最新版的高分子物理教材中!另一方面,四十年代末,现代非平衡统计开始发展,源自非理想气体的多体统计力学的方法学也逐渐成熟。这些基础理论成果很快被用于高分子问题。特别是60年代以后,这些新发展事实上已经成为现在软凝聚态物理的教科书内容,但在当年Flory充当的角色常常是旁观的、批判的;仅偶尔作一些跟踪的研究。
我国现行高分子物理教学体系对于Flory之后的新进展,似乎只重视法国的de Gennes的标度理论——这其实只是物理学的一种“玩法”,但从国内教科书的写法来看,似乎这些作者也没“玩”明白。若说de Gennes把链看作分形从而以临界现象的语言来描述结构;英国的Edwards则通过把链看作可求弧长(retifiable)的光滑流行,从而用变分法和路径积分的语言来描述结构。后者哺育了自洽场理论。那么美国的特点则是更加直接(straight-forward)的基于粒子的经典非平衡统计。
50年代始的日本高分子研究
日本的寺本英(Ei Teramoto),应该是最早把集团积分的方法引入高分子问题中的科学家。他在1951~1952年左右集中发表了真实链(体积排除效应)的统计力学理论方法。他带领山本三三三(Misazo Yamamoto)和松田博嗣(Matsuda Hirotsugu)做的工作,既包括格子统计,又包括连续空间的统计,基本上都发表在《物性论研究》杂志上。这些工作是领先世界的。
50年代,日本人在格子链的格子统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早在1941年Bethe作了“准化学近似”工作的同年高木豊(Yutaka Takagi)就在日本数学物理学会记事第3期发表了相同的工作,因此日本人常称这个近似为“Bethe–高木近似”。至于3维格子链的各类非平均场近似,自30年代在Fowler、 Guggenheim和我国科学家张宗燧(见我之前的另一篇文章)以来,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就是我国的杨振宁、李荫远和日本的藤代亮一(Ryoichi Funshiro)、石原明(Akira Isihara)、菊池良一(Ryoichi Kikuchi)、水谷宽(Hiroshi Mizutani)和寺本英的数学工作。寺本英带领的倉田道夫后来又独立地与横浜国立大学的亘理達郎(Tatsuro Watari)继续发表格子模型的更精确的近似。据倉田道夫回忆(译自日文):
将高分子研究引入田村研究室的,是首位毕业论文生岩崎浩一郎。临近毕业之际,他不知从何处弄来高分子样品开始测量固有粘度,在杂志会上介绍弗洛里排阻体积效应理论,并高呼“未来属于高分子时代”,随后便进入三菱化成公司任职。此事发生于1950年3月。
同年,由理学部的寺本英、工学部的稻垣博、农学部的藤田博等人发起的高分子研讨会成立,我也参与其中。该学会后来催生了寺本先生等人提出的排斥体积效应的微扰展开理论,以及山本三三三先生提出的聚合物粘弹性拟网格理论。我亦与亘理教授合作,运用团簇变分法发展了聚合物溶液理论。
山川裕巳(Hiromi Yamakawa)就是Modern Theory of Polymer Solutions一书的作者。他是桜田一郎的学生。上述这本书中溶液统计部分就是他的博士论文工作,而书中关于真实链统计的工作,其实是始于寺本英。他向寺本英和倉田道夫学习了的统计力学方法,结合了McMillan–Mayer巨正则系综,讨论溶液中的聚合物链统计。链统计的工作已经明确了非高斯假定下均方末端距和均方回转半径是关联弱化了的两回事。而在溶液中,链的扩张性来不是来自链本征排斥体积效应,而是溶剂链段相互作用的等效排斥体积效应,这又使得第二位力系数、 theta条件的特性粘数、无扰均方回转半径之间的关系也是弱化的。Zimm, Stockmayer和Fixman在1953年发表的工作,在简化势能参数$\beta$下,说明所有这些量都能表示为关于$z\sim\beta N^{1/2}$的展开,但他们只给出了一階近似。山川就链统计问题的均方末端距和回转半径给到了高階近似,就特性粘数的扩张比和Flory–Fox特性粘数公式的那个$\Phi$系数,Kirkwood–Riseman只给出了theta条件下的结果,山川给出了良溶剂下的一階近似。
山本三三三后来也疑似领先于Lodge和Green–Tobolsky给出粘弹性的微观模型。英文世界一般引用他1958年发表在J. Phys. Soc. Jpn.上的三篇论文,但是早在1952年始,他就在《物性论研究》杂志上发表系列工作。他的这个模型也许是最容易被日本研究者了解的,因此也支持日本人很早就跟踪高分子溶液的非线性粘弹性实验研究,例如田村幹雄(Mikio Tamuro)带领倉田道夫(Micho Kurata)、小高忠男(Tadao Kotaka)进行Weissenberg效应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就常拿山本三三三的模型进行比较,使得日本流变学研究在英语世界以外就自成体系。
更不利的条件,其实还是语言的问题。许多工作最早发表于日文期刊,然后要么没再发表,要么隔两三年才再以英语发表到美国期刊(当时我们还很难说这些期刊是“国际的”)。比如中川鹤太郎应该是“最早之一”(among the first)研究Weissenberg效应的。因为这个效应广泛成为其他研究者的课题要等到Weissenberg的“流变测角仪”(Rheogoniometer)商用化之后。 我师爷藤田博当时可能通过美国关系(他在美国熟人很多)搞到了Roberts的供应部报告ADE13/52——这是数年后Weissenberg的流变仪商用化的基础,根据这份报告小高忠男仅耗资两万日元手工制作了一个实验装置,由此在1956年倉田道夫和小高忠男就成功阐明了法向应力与非牛顿粘性的关联系,但是在1960年因论文评审不幸延误而错失国际优先权。他们的发现是:高分子溶溶液的稳态粘度基本不依赖分子量。
遍览1950年代日本的高分子物理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论是先进的,而且成果是领先的。日本高分子物理的理论研究,从跟踪到领先,只花了十年。
1953年Flory到日本访问
1953年,国际理论物理会议在京都举行。其中有一个聚合物symposia,Flory和Kirkwood都去了,各作了一个报告。日本方面,寺本英作了链统计的报告,石原明作了橡胶弹性的一个非高斯理论的报告。如果我没对应错,他具体作的是考虑了真实链(位阻效应)之后,不仅在大形变下而且在小形变下也偏离高斯链预测的结果。Flory一直都对1950年以前的的橡胶弹性分子模型版本十分defensive,他反对任何破坏原始的那几条简单假定的新说法。所以Flory对石原明的报告就是批判的,要么说大形变有啥不对都怪结晶,你没做X线排除就啥也不能说。要么说小形变还有Wang & Guth的工作说明也不一定就怪非高斯。
Flory和他的其中一个门生J. E. Mark在回击新的橡胶弹性理论这件事情上,频繁运用的技巧就是confirmation bias,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双标”。关于这件事,我可能会在另一个文章中专门去扒。
至于寺本英报告的链统计工作,Flory则不得不承认是“among the first”。但Flory还是老强调他自己推的那个$\alpha^5-\alpha^3$,其实他就还是以为只有一种无扰尺寸且只有一种扩张比。Kirkwood & Risemand在1940年代的工作就已经暗示溶液的特性粘数扩张比跟尺寸扩张比是两回事了。Flory常常喜欢强调的就是,我也做了这问题,也有一个结果;却认识不到新的物理方法的先进性带来的认识的深入。
同一场会议,参会的倉田道夫又是怎么描述的呢?
1953年,战后首次国际会议——理论物理学会议在京都召开。受邀在会上作报告的寺本先生,计划结合已完成的微扰理论,公布通过二维正方形晶格链的全部配置检查所获得的排斥体积效应“实验值”。不难想象,此类检查的工作量会随着链条长度的增加而呈指数级增长。最终我协助整理出了链长不超过20的实验数据。紧随弗洛里教授之后登场的寺本先生演讲堪称压轴之作。正是通过这项实验,我终于领悟了排斥体积效应的本质,并由此获得了后续理论研究的长期展望。当时纵观全球,真正理解该效应者仍属凤毛麟角。
但至少,在1953年Flory访问了日本,很难会说出他1978年访问中国所说的那句话:中国还没有高分子的基础研究!从今天我们的高分子物理教材内容来看,我们的高分子物理也没超过1978年的理论,更别说能出几个“among the first”了。再贴一次开头贴过的任鸿隽文字:
国人向学之诚。自近世科学之术。愈益发达。凡人群所待以为用之智识。有条理伦脊可抽绎者。莫不列为专科。从事研究。明而政治经济。玄而哲理数术。大而建船筑路。细而日用服食。皆得于学校教育占一席焉。其教育之旨。多在致用。致用之极。于是有浅尝肤受。得一能自给。充然自以为足。而无复深造之想者。夫今之科学。其本能在求真。其旁能在致用。上治之国。其制度厘然。物质灿烂者。无非食科学之赐。致用之无害于科学。又何待言。顾无委心专志。发愤忘食之科学家。积其观察之勤。试验之劳。思辨之能。为之设立公例。启示大凡。令后人得循序渐刊以抵高明之域。则近世欧洲学界。仍如中世之黑暗可也。是故建立学界之元素。在少数为学而学。乐以终身之哲人。而不在多数为利而学。以学为市之华士。彼身事问学。心萦好爵。以学术为梯荣至显之具。得之则弃若敝屣。绝然不复反顾者。其不足与学问之事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