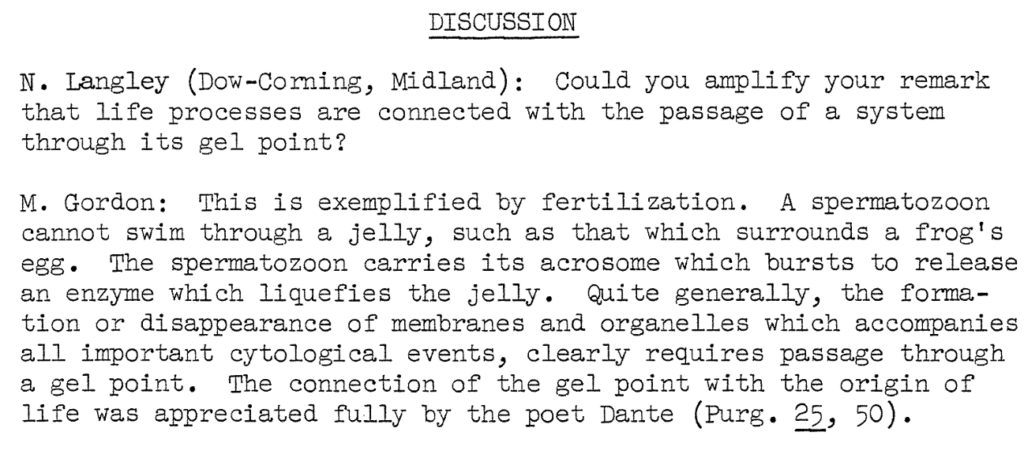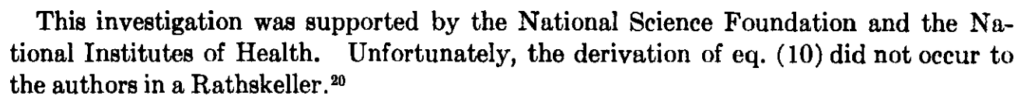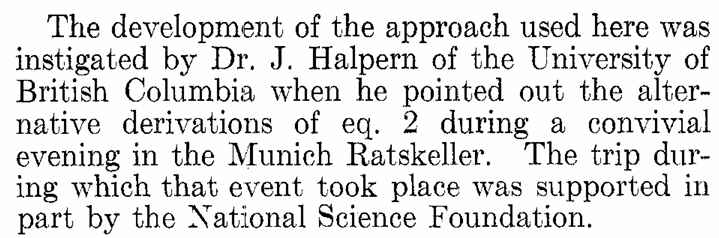在 1960 年代,大家普遍相信:对某一特定化学物种的高分子链,“无扰尺寸”(unperturbed dimension)是唯一的,等效高斯链段长度与链段数这些参数应该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用任何实验手段测出来的无扰尺寸都应该一致。 那个年代最常用的路线是稀溶液粘度法;而从理论上讲,无扰尺寸主要受键角与内旋转受限性影响,所以配合 旋转异构态(RIS)理论 计算就可以做出预测。
但是到大约1970年前后,越来越多现象提示:即使把溶剂调到theta条件,溶液粘度测到的“无扰尺寸”仍可能随溶剂而变,这等于在提醒我们——溶剂并非只是把排斥体积效应“关掉”,它还可能通过影响链的内旋转势能分布而改变构象统计。 那么问题就变成:所谓“无扰”究竟应该以什么状态来定义?如果回到RIS计算的出发点——单链统计——去定义一种“理想的无扰状态”,但这种状态在原则上未必对应任何现实中可直接制备的试样,因为高分子没有气态。
在这种背景下,Flory相信熔体中的链可能最接近他所说的无扰链,因此当小角中子散射(SANS)技术刚出现时,他很积极地推动大家去做高分子熔体实验,用来检验他在书中与论文里给出的预测。 这类实验的关键技巧之一,是把少量氘化链掺到未氘化的基体中,利用氢/氘在中子散射截面上的巨大差异,从而在“结构上几乎不改变体系”的前提下把单链信号“显影”出来,进而提取均方回转半径等量。 在没有SANS之前,确实缺少这样直接、干净地在凝聚相里看单链统计尺寸的办法。
但实验并没有把事情简单化:某些极性聚合物的熔体结果与理论预测差得很远,甚至也与 theta 溶液的结果差很远。 这类现象被称为“凝聚相效应”(condensed phase effect):链间相互作用会让熔体中的链构象势能分布不同于“孤立单链”的分布。 也正因如此,把单链理论直接搬到多链熔体上,有时只能算是一种 phantom chain / polymer gas 的近似。
Flory在斯坦福之后更集中地做链构象统计。他大量做 RIS 计算大概主要在1970年之前。他的重要著作《Statistical Mechanics of Chain Molecules》在1969年出版,这本书里很多推导与结果带有“手算时代”的痕迹,因此对更高阶相关的处理会受到限制;后来大家转向电子计算,很多动力来自于想把高阶相关系统化算出来。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他利用斯坦福大学的IBM大型计算机中心(该中心因美国登月计划的需求而兴起民用),成为首批将电子计算机用于科学研究的研究者之一。RIS计算需要关于不同构形下侧基-侧基相互作用势的输入,手算的话,只能把沿链太远的相互作用忽略掉,大概只有二阶相关的结果;使用计算机就是为了算高阶相关,后来发现这对极性高分子来说是不可忽略的。原子间的相互作用势数据,原本也是半经验估算的;再往后,量子化学第一性原理方法逐渐成熟,才使得“相互作用势从头算”成为可能,这是Flory当年未必来得及亲眼看到的演进。
弗洛里将高分子链统计物理这条研究路线一直推动到他1985年去世。这条路线与后来皮埃尔-吉勒·德热纳(Pierre-Gilles de Gennes)发展的标度理论是并行的、不同的路径。许多场合人们喜欢用一种话术叙述历史:“Flory预测A,但标度理论预测B,实验发现de Gennes对”,这会让不熟悉的人误以为是前者被后者全面推翻。在我看来,de Gennes与 Edwards等人在很多关键问题上进入的是Flory当时没有覆盖、或者当时社区还没意识到必须更新物理机制regime——尤其是多体相互作用不可忽略、凝聚态效应不可忽略的情形,例如半浓溶液等。 而且de Gennes的一些关键直觉与机制,和欧洲液体物理的发展脉络关系很深;他当然把这些东西带进了高分子,但把这段来源抹平之后,就容易被讲成“完全原创、凭标度技巧平地起高楼”。Edwards早年在Gee的影响下从橡胶弹性问题进入高分子界,最初的动机之一与解释Mooney–Rivlin形式里某些参数(例如常被称作 的那一项)为何不为零有关。 后来围绕“约束”的语言体系逐渐丰富:缠结只是约束的一种,局域约束还会引出更一般的非均匀性/异质性(heterogeneity)表述;而Flory自己更愿意维护他与Erman关于“交联点运动受限”的解释路径,并不轻易在语言与框架上向后来那套液体物理/相变理论化的表述让步。这算是Flory直接对“下一个范式”的有什么直接反应的仅有记录了。